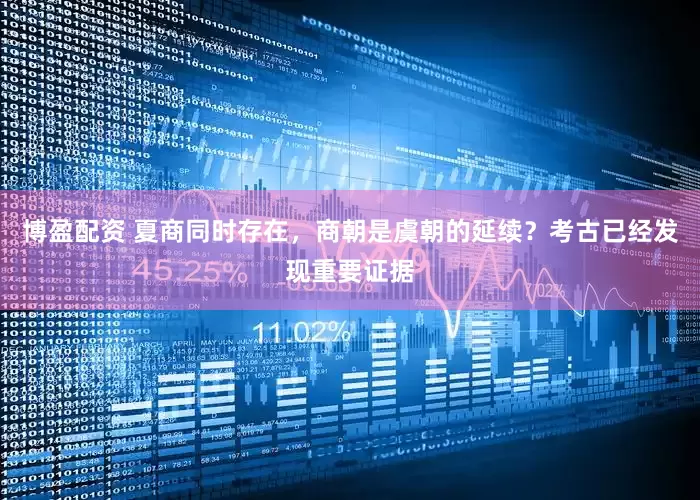
重写版:
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大禹成功治理洪水后,被推举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。他的儿子夏启后来夺取权力,取代了原本的继承人伯益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。当时,商族只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。四百年后,夏朝最后一位君主夏桀暴虐无道,商部落的首领商汤以替天行道为名,推翻了夏朝,建立了商朝。
然而,现代考古发现却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夏朝和商朝很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先后继承关系,而是曾经同时存在过。更令人惊讶的是,商朝可能直接继承了更早的虞朝的文化传统。让我们来看看相关证据:
关于商族的起源,历史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主要观点:东夷说和北方说。
支持东夷说的证据主要有三点:首先,《左传》中提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(商契)居商丘,这里的商丘被认为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;其次,商族人崇拜玄鸟,这与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相吻合,东夷首领少昊就被称为百鸟之王;第三,商朝灭亡后,周朝将商朝遗民封在宋地(今商丘睢阳区),这似乎暗示这里是商人的发源地。
展开剩余80%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考古学家在河南商丘地区始终未能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先商时期遗址。相反,在河北和河南北部却发现了大量先商文化遗址。比如在石家庄发现的平山西门外遗址和鹿泉北胡庄遗址,后者被专家评价为填补了先商文化研究的空白,证实了滹沱河流域是商族祖先的发祥地。
在河北石家庄到河南濮阳一带,考古学家发现了漳河型先商文化遗址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邯郸北羊井遗址。在濮阳还发现了跨越龙山文化到夏商周三代的古高城遗址。在濮阳与郑州之间,则分布着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。这些发现表明,商族人很可能是从北方逐步南迁,最终逼近夏王朝的核心区域——伊洛平原。
通过这些考古发现,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商丘的真正位置。虽然史书记载商契的都城商丘可能在今河南商丘或濮阳,但从商族南迁的路线来看,更可能是在濮阳一带。
关于商族的始祖,《史记》记载商周两族都是帝喾的后裔。但先秦文献《国语》和《礼记》却给出了不同说法,暗示商族可能奉帝舜为始祖。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:如果帝喾和帝舜不是同一个人,那么帝舜封其子商均于商地时,商契的封国应该已经不存在了。但甲骨文中明确记载商契是商人的祖先,这说明商契的封国并未灭亡。
甲骨文中出现的高祖夒和高祖夋(夋通俊)被认为就是传说中的帝俊,也就是商人的始祖。东晋学者郭璞指出俊字也可以读作舜,因此帝俊很可能就是帝舜。这样一来,帝舜、帝喾、帝俊很可能是同一个人,是商族的始祖。而帝舜是虞朝的统治者,商族自然就是虞朝的继承者了。如今,濮阳被称为帝舜故里,近年发现的高城遗址也为这个说法提供了考古证据。
这意味着在夏朝建立之前,实力强大的帝舜(商族始祖)可能定都于濮阳。这样一个强大的部族,在帝舜去世后真的会臣服于夏族吗?考古发现似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
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二里头遗址以来,经过70多年的研究,学者们发现了一些矛盾之处: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处于尧舜到商代之间,理论上应该属于夏朝时期。但二里头早中期并没有表现出广域王国的特征,更像是一个地方政权。直到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,才显示出王朝气象。那么,夏朝前中期的都城在哪里?
河南新密的新砦遗址(约公元前2050-前1750年)拥有城墙、壕沟、精美玉器和铜器等,具备都城特征。但该遗址带有明显的东夷文化色彩,可能与后羿代夏的历史有关。更重要的是,新砦类遗存主要分布在郑州地区,范围有限,说明当时夏可能只是一个地方政权。
辉卫型先商文化已发现20多处遗址,分布在太行山以东、淇河以南、黄河以北的广大区域。其中鹤壁刘庄遗址发现了336座墓葬,出土了象征权力的石钺、石棺等500多件文物;辉县孟庄遗址除了礼器外,还发现了完备的城防系统。这些发现表明,当时的商族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。
这些遗址的年代大约对应商族第七代首领王亥时期(约公元前1874-前1775年),与夏朝新砦遗址同期。从考古发现来看,夏商两族很可能是并存的,商族臣服于夏朝的可能性很小。
甲骨文记载最早称王的是王亥(商汤的六世祖),与夏后泄同时代。这说明当时商族已经是能与夏朝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。二里头遗址的下限是公元前1530年,而附近的偃师商城(被认为是商汤的都城西亳)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,两者相距仅6公里。这意味着夏商两朝有近100年的共存期。
这可能说明,在夏商时期,中国大地上可能同时存在多个强大政权,就像后来的宋辽夏或宋金夏时期一样。周代人可能用当时的朝代观念来看待夏商时期,将夏朝视为正统王朝,而实际上当时可能是多个政权并立的局面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华安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